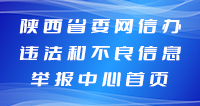熬一锅朴素的乡愁
来源:榆林日报
时间:2026-01-30 09:01:17
编辑:张倩
校对:李娜
责编:王丹
腊八是要喝粥的。在陕北,腊八的粥不叫粥,叫“粘饭”。一个粘字,道尽了它的性子,也道尽了这节气里的冷暖。
时令进了腊月,风就硬了,刀子似的在塬上刮。天是那种干冷干冷的灰白,地冻得裂开无数细小的口子,像老人手背上的纹。窑洞是暖的,和着炕头的温度,把人裹得严严实实。就在这当口,腊八来了。
我母亲天不亮就下炕了。豆子是早几日就拣好的,红豆、绿豆、豇豆,还有陕北特有的钱钱豆,黑是黑,白是白,各自盛在粗瓷碗里,炕头摆一排,看着就喜庆。水是从沟底挑上来的泉水,冰得扎手,母亲说,这样的水“有筋骨”,熬出的粥才黏稠。红枣是自家院里枣树结的,晒得蔫皱了,一入热水,便慢慢丰腴起来,皮儿涨得发亮。
灶火起来了,用的不是煤,是晒干的玉米芯和修剪下的树枝。火舌舔着锅底,跳跃的黄光,把母亲的身影投在窑壁上,忽大忽小。她添水,下米,金黄的小米先下,然后是各色豆子,最后才是红枣、核桃仁和钱钱。一锅水渐渐便有了颜色,有了动静。起初是咕嘟咕嘟地冒着小泡,像是地下泉在低声说话;慢慢便沉稳了,表面凝起一层厚厚的膜,底下却在看不见的地方,汹涌着。
这熬煮的过程是极慢的,慢得像这陕北高原上冬日的时光。母亲坐在灶前的小凳上,并不总盯着锅,手里或纳着鞋底,或只是静静地望着火。火光在她脸上明明暗暗,她的神情是平和的,甚至有些木然,仿佛她的魂灵也有一部分化在了这氤氲的蒸气里,和那些米啊豆啊一同熬着。只是偶尔用那柄长长的木勺,伸进锅里,顺着一个方向,慢慢地搅上几圈。那黏稠的粥被搅起来,又沉下去,拉起一道道琥珀色的、绵密的丝。
香气是一点点溢出来的。起初只是粮食被火烘着的那种朴素的香;接着,豆腥气被熬掉了,变成了醇厚的暖香;最后,红枣的甜、核桃的油润,全被逼了出来,融在一起,那香气便有了重量,沉甸甸地充满了整个窑洞,又顺着门缝窗隙钻出去,飘在清冽的空气里。这香气,不像花香那样飘忽,倒像是一种实实在在的、可以触摸的东西,像一块温暖的、甜软的毯子,把腊月里所有的严寒和空寂都隔绝在外了。
这粥的“粘”,是有说法的。祖母在世时常讲,喝了这粥,能把人的下巴粘住,说不了闲话;能把一家人的心粘在一处,散不了;能把来年的好光景“粘”到家门里,跑不了。你看那一锅粥,米不再是米,豆不再是豆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粘粘乎乎地团成一气,分拆不开,这不正是一家人过日子的模样么?
粥熬好了,母亲盛出头一碗,稠稠的,供在窑壁正中那块小小的神龛前,这是规矩,是对天地神明的感念,感谢这一年的风调雨顺,五谷平安。供过了,才轮到人。一人一大碗,不兴用勺子,得双手捧着碗,沿着碗边,小口小口地吸溜。那粥滚烫,粘糯,顺着喉咙滑下去,一条热热的线直通到胃里,然后那暖意便从身体最深处向四肢百骸扩散开去,指头尖都感觉麻酥酥的。喝到鼻尖微微冒汗,寒气便从骨头缝里被逼了出来。这时再嚼到一颗煮得开了花的红豆,或是半颗软烂的枣,那甜,是沁到心里的。
有一年,父亲在腊八前出了远门,说好腊八晌午赶回来。那天,母亲照例熬了粥,比往年更黏稠。粥在锅里温着,从晌午等到日头偏西,热气一遍遍续上。我们小孩子饿得肚子叫,眼睛直往锅里瞟。母亲只说:“再等等,你大快回来了。”直到天擦黑,风里才传来熟悉的脚步声。父亲带着满身的寒气进来,胡茬上都凝着白霜。母亲不言语,只盛了满满一碗粥递过去。父亲接过来,也不怕烫,大口地喝。窑洞里静静的,只有他吸溜粥的声音。那一碗粥下去,我看见他冻得发青的脸色,才一点点缓了过来,有了活气。那一顿腊八粥,是我记忆里吃得最晚,也最踏实的一顿。
如今,我坐在城里的暖气房中,窗外没有塬上的烈风,灶下也没有枣柴的明火。超市里有配好的八宝粥料,电饭煲一个按键,便能得一锅甜粥。快是快了,也便捷,可总觉得缺了点什么。缺了那漫长等待里,被火光和蒸气熏染出的耐心;缺了那各种滋味在时间里,真正交融在一起的醇厚;更缺了那捧着一碗滚烫的粥,从指尖暖到心里的、对抗整个寒冬的郑重。
今年的腊八,我为自己熬了一锅粥。我熬的不只是粥,是一段被熬煮得黏稠了的时光,是黄土高原在腊月里,用风霜与烟火为我酿造的一碗,最朴素的乡愁。
李宁

 陕公网安备61080002000253号
陕公网安备61080002000253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