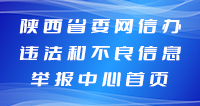儿时的“书屋”
来源:榆林日报
时间:2026-01-24 10:56:53
编辑:李强
责编:王丹
府谷县城过去的老书店在十字街,随着县城的发展,书店搬迁,这里又先后成为粮店、饭店,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,在我记忆里永远留着儿时“书屋”的影子,每当路过,都不由得驻足良久,勾起儿时温暖的记忆。
书店对于我是儿时的精神食粮,是一扇观察世界的窗口,每当来到这儿,便像是饥饿的人扑向面包,如饥似渴。其实比起现在,当时的书店并不阔绰,甚至十分简陋,面积不大,书橱也不亮眼,冬天没有暖气,屋中央烧着大洋炉子,地面是砖铺的,坑坑洼洼,陈列的书籍种类单调,数量也不多,在现代人眼里落后陈旧,但在五十年前的县城,却是精神文化圣地,一颗镶嵌在县城腹地的明珠。
我跑书店是从六岁开始的,当时我随父母从关井搬到前石畔,还不到上学年龄。当时没有幼儿园,上学之前,玩就是主要生活,书店是最好的去处。去了书店怯生生地站在书橱前,好心的阿姨看着我每天到书橱前盯着半天都不走,便拿本连环画让我看,我看得专注到忘了回家吃饭,渐渐地成了书店的常客。
书店的书是用来卖的,看一下可以,但常看不买是断然不行的,售书阿姨虽然满眼是爱心,但因制度所限,渐渐地我白看连环画的资格被剥夺了,一下子陷入绝望。问父母要钱买书根本不可能,当时家家生活都紧张,谁都不会支持学前孩子买书,认为是瞎害钱,我在巨大渴求下尝试了几次都无果而终。
我想到了爷爷,虽不是亲的却胜过亲的。爷爷之前未娶,快四十岁才娶得改嫁过来的奶奶,父亲作为继子在爷爷的培养下上学工作,娶妻生子,我和姐姐都是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的,常记得儿时一觉醒来就能看到两位老人煮得热气腾腾的饭菜。爷爷是老党员,对革命有功,是当时立新总店的负责人。立新总店其实是一家老式的商铺,主要经营烟酒副食。爷爷常常端着旱烟袋,眯着眼,立在柜台前,管理员工,主持着店里的生意。
我溜去爷爷工作的商铺,像乖猫一样站在墙边,爷爷慈祥地笑着,把旱烟袋收起,从衣服里掏出一两角发皱的纸币塞到我手里,让我买糖果零食,我兴奋地一溜烟跑了。一两角钱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购买力可不小,当时五分钱可以买张电影票,两分钱可以买根雪糕,拿到一两角钱,对于我这样一个几岁的孩子来说是一种莫大的满足。于是我慎重地安排支出,先买两本心爱的小人书,再用剩余的钱买点儿零食,喜滋滋地跑回家,享受这顿精神物质俱佳的“大餐”。打开崭新的连环画,一股墨香弥漫了整个屋子,书里的人物画面仿佛一下子动了起来,与我相视对话。往后,我便隔三岔五地去爷爷那里“蹭钱”,爷爷从不拒绝,总让我有收获。老人一辈子没有生养,把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外姓人当作至亲,想来都热泪难禁。
书店的书毕竟不是随时都能买得起。自己的书不够看,就向别人借。我现在仍清晰地记得医院家属区有一对叫杨林、杨杰的双胞胎男孩,比我小一两岁,我们很合得来,在一块常常玩得很开心。他俩家庭比较宽裕,父母是北京来的大学生,收入在当时算比较高的。他家的书很多,特别是小人书一套一套的,《水浒》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《岳飞传》等应有尽有,因为和他们的关系好,我常借书看。
稍大念书识字后,读书的内容在扩展。书店作为儿时的“书屋”,仍然是我的至爱,但连环画变成有字之书,由直感的画面变成文字的记忆。购书方面除了四大名著外,还买过《围城》《三家巷》《青春成岁》《周恩来传》《人生》,还有巴金的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,茅盾的《子夜》,鲁迅的《朝花夕拾》等等,读遍天下书,对于一个少年旺盛的求知欲来说也不算夸张的目标。
紧挨书店有个阅览室,在我的记忆里好似专为我安排的,和书店形成天然一体的“书屋”。书店有选择购书的功能,阅览室则是书店的延伸,是读书休憩的场所,我在书店购书后往往到阅览室阅读。阅览室还有各类报刊杂志,环境很安静,有读书的氛围,大家都在静静地阅读,绝无半点嘈杂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,中国处于经济文化复兴的起步阶段,小县城率先由几大民营企业家掀起经济发展的狂潮。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文化复兴也悄然兴起,学习进取的风气遍布城乡。十字街地处县城核心区,是县城的政治文化商业中心,既有繁华的商贸集市,也有书店影院等文化设施,在喧嚣的经济繁荣背后,潜藏着文化复兴进步的洪流。我的儿时“书屋”是县城历史剧变的一部分,围绕儿时“书屋”展开的个人生活成长已成为历史缩影。
王小林

 陕公网安备61080002000253号
陕公网安备61080002000253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