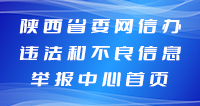父亲的红眼睛
来源:榆林日报
时间:2026-01-10 00:31:46
编辑:李 娜
校对:李强
责编:王丹
那抹红,从我记事起就嵌在父亲的右眼——下眼睑外翻着,像片揉皱的红绸。三十多年前父亲入殓时,全家人执意给他戴上石头眼镜,仿佛要将那抹红妥帖藏进永恒的黑暗里。可直到今天,那只眼睛仍在我记忆里亮着,像粒未爆的火星,灼着一个未解的谜。
父亲的红眼睛,让我小时候受过不少嘲笑,也流过无数眼泪。记得上小学时,有个比我高大、年长的同学,常故意在我面前拉下自己的眼睑,露出红肉来嘲笑我。我气得使出吃奶的劲儿想让他停下,却总以失败告终。最让我痛心的是我的女同桌小丽。她父亲是干部,她穿得又新又干净,模样可爱,我那时懵懂地想,将来就要娶这样的姑娘当媳妇。可有一次,她也撇着嘴,带着点轻蔑的语气对我说:“你爸是个红眼眼。”这句话像针一样扎进我心里。从此,我在桌上划了一道深深的“三八线”,只要她的胳膊肘越界,我就毫不客气地一肘子顶回去。更可恨的是绰号叫“五喜”的同学,他为了哗众取宠,竟拿父亲这块“短板”编成顺口溜羞辱我和父亲:“红眼眼狼扯疤,种的麦子犵狸(松鼠)掐!”他学习不好,顺口溜也编的牛头不对马嘴,这算哪门子话?父亲的眼睛跟麦子、松鼠有什么关系?五喜是个连老师都不敢惹的狠角色,我哪敢跟他硬碰硬,只能低声嘟囔骂一句来泄愤。
这双红黑交织的眼睛,也曾亮得让我发烫。生产队秋收时,我撞见有人往怀里塞高粱穗,回家告诉了父亲。后来可能是父亲反映给了队长。过了几天,天刚蒙蒙亮,我还在被窝里,那人就冲到我家,厉声问我:“甚时候看见我拿队里的高粱穗了?”我吓得不敢吱声。父亲正蹲在灶台前添柴,火苗在他眼里跳。“又(我的小名),照实说。”他声音不高,红眼珠却亮得惊人。我梗着脖子说完,那人悻悻走了。父亲往灶里添了把柴:“见了这种事就得说,谁让他有脚手不稳的毛病,邪不压正。”听着父亲的话,我心里顿时暖烘烘的。那天的灶火格外旺,把他的红眼映得像团火。
20世纪70年代初,307国道吴堡至绥德段要从石子路改铺柏油路。我们全家老小齐上阵,起早贪黑地砸石子,想给家里添点进项。快量方算钱的时候,我耍了个小聪明,偷偷把一块大青石埋进石子堆里,想多算点方量。结果埋得太仓促,石块一角露了出来,被量方的工作人员一眼发现。他用耙子一扒拉,大石头就露了馅。“老张,可不能这么占公家的便宜啊!”工作人员的话让父亲脸上挂不住。他猛地转过头盯着我们兄弟三人,厉声问:“谁埋的?”那只本来就红红的眼睛这时的充血量达到极限,眼看事情败露,不等父亲的手扇过来,我扭头就跑。夜里缩在炕角等着挨揍,他却只站在炕前骂:“鬼仔子,公家的便宜能占?以后再敢胡日鬼(捣乱),小心我扳断你的嫩骨石!”月光从窗棂漏进来,照见他眼里的红褪成了暗紫,像燃尽的炭。那年我十岁出头。
1978年春天的一段时间,父亲一黑一红的眼睛里闪烁着希望的光芒,听说政府有政策,给参加过八路军的人发放补贴,少说一个月也有十来块钱。那段时间,父亲隔三差五就往县城跑。父亲确实在延安当过八路军。如果能领到这笔补贴,对我们这个贫寒之家来说,简直是天大的好事。母亲私下跟我说:“不晓得咱有没有那个福气,要是能办成,你以后的学费就不用愁了。”是啊,那时我上高中,一个月五块钱的伙食费,每次回家取钱,总看见母亲紧锁着眉头。其实我头一年就该上高中,就因为三哥还没毕业,家里供不起两个高中生,只能推迟一年,等三哥毕业了,我才上。父亲是家中长子,兄弟五个。抗战期间,他被征召去了延安参加八路军,分在保育院后勤组,主要任务就是给保育院的孩子们担水做饭。父亲说他一天要担二三十担水,起初肩膀都压肿了,苦很重。后来不知得了什么病,就病退回老家了,由我二爸顶他当兵。
县民政局要求父亲出示当年的病退手续,才能证明他八路军的身份。全家人把屋里屋外翻了个底朝天,连墙缝和老鼠洞都掏了,硬是没找到那张纸。那时奶奶还在世,父亲问她,奶奶恍惚地说:“兴许……兴许是我糊了纸面洞(做纸糊的容器)了?三十来年了,早让老鼠啃了吧?”父亲又去找民政局领导,领导说手续找不到,还有个办法是找两个当年一起当兵的人证明。父亲一黑一红的眼神里充满了无奈:“我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,当年一起当兵的南腔北调,离开部队就再没联系,上哪儿找证明人去?”最终这事不了了之。
这抹红到底是怎么来的?母亲说是累的,我猜是延安的风霜刮的。直到前年见了八十岁的姑姑,她说:“你爸去当兵前就眼疼,总说扛扛就过去了,那时候医疗条件也不行……”我突然想起父亲给我刨锄把的模样——左眼瞄木把的直弯,眯着右眼的那抹红在晨光里闪光,像片不肯熄灭的火星。
如今我也老了,偶尔对着镜子看自己的眼睛,总想起父亲。其实谜解不解,又有什么要紧?他早把最清亮的东西,种进了我心里。
张建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