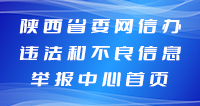大雪深处是故乡
来源:榆林日报
时间:2025-12-08 09:02:04
编辑:郝莉娜
责编:王丹
节气这东西,是刻在骨子里的。任凭走得多远、离开多久,一到时令,魂里梦里便生出感应。此刻,城里的冬日慵懒,窗外天色不明不暗。可我心里却无端地一紧,空落落的,像是被什么又硬又冷的东西硌着了。我知道,是“大雪”来了——不是日历上那个单薄的黑字,而是从祖母那盘滚烫的土炕上,越过千山万水,直直撞进我心口的那个真正的大雪。
节气一到,故乡的天地就褪尽了最后一丝温柔。风成了主角,从更北的荒漠席卷而来,失了水分,只剩刀刃般的锋利,在光秃的梁峁间来回刮削,呜呜作响。田埂边几丛枯草瑟瑟发抖,是它仅存的玩物。天空泛着僵冷的青灰,像口倒扣的巨大铁锅,把整片黄土高原严严实实地罩住。人站在外面,只觉得风能穿透厚厚的棉袄,直往骨头缝里钻。世界仿佛被抽干了,只剩下坚硬与沉默。
但天越冷,窑洞里的人情越暖。一钻进挂厚棉帘的窑门,就像踏进了另一个世界。所有的寒冷与呼啸都被关在身后。扑面而来的是扎实的暖流,混着烟火、馍香和泥土的气息,不由分说地将你拥入一个等待已久的怀抱。
这温暖的源头,是炕、是灶、更是人。
我总想起祖母,大雪天里,她几乎和那盘土炕长在了一起。一双小脚的她,炕就是她的江山。终日盘腿坐在炕上,守着紫红色的旧炕桌,桌上永远摆着针线笸箩。她不常做活,多数时候就这么静静坐着,干瘦的手一遍遍、极缓极缓地摩挲着温热的炕席。高粱秆编的席子,年月久了,被体温磨得油光水滑,泛着深沉的琥珀色。我那时顽皮,在炕上打滚,一抬头,总看见她眯着眼望麻纸糊的窗格子,眼神空茫又笃定,像是要看穿那层薄纸,看到很远的地方;又或者,她什么也没看,只是感受这窑里的温暖。如今想来,那神情竟似土地庙里的神像——一种与岁月和解后的无言慈悲。
满窑的暖意,全靠窑掌里那口大灶维系。一入大雪,灶火便日夜不熄。父亲劈的硬柴在灶膛里轰轰燃烧,火苗富足欢腾,灯光把母亲忙碌的身影一会儿拉得老长,颤巍巍地贴在窑顶,一会儿压得极短,缩在灶角。锅里总煮着东西——喂猪的洋芋、南瓜,或待腌的年肉。白蒙蒙的水汽蒸腾弥漫,连灯光都变得柔和迷离。人在水汽里说话,声音也濡湿了,带着满足的慵懒。
灶火还酿造着专属于大雪的香甜。那是吊在灶口上方、日日熏着的年糕。秋日新打的黄米,蒸熟捶打,切厚片用麻绳穿起,一串串挂在灶膛口。日子久了,糕体渐渐染上温润的烟色,像浸透了时光的蜜。它贪婪地吮吸着三餐时分升起的、带着五谷油脂香气的暖烟,水汽一丝丝逼走,换来紧实韧韧的醇厚甘甜。我那时最馋这个,常仰头看烟色一日深过一日,心里便一日日积攒起对年关的期盼。祖母见我猴急,慢悠悠说:“傻娃娃,急甚?火候不到,滋味就薄。人活着,也是一样的道理,得耐得住。”
她的话,我那时自然不懂,只觉等待漫长,是甜蜜的折磨。
大雪的夜又是另一番光景。我在暖得发烫的被窝里沉入梦乡,窗外的北风愈发狰狞,在窗外凄厉嚎叫,用身体冲撞窗棂,仿佛下一刻就要破窗而入。世界被这声音衬得愈发寂静,愈发显得这孔窑洞是洪荒中唯一安全的孤岛。这时,祖母会下意识把我往她怀里拢拢。她那干瘦的身子,竟如火炭般热。半梦半醒间,听着骇人的风声,感受祖母的体温,这窑里的温暖,珍贵得像不容惊破的梦。
多年后,置身恒温洁净的寓所,被无形的焦虑围困时,我才骤然明白祖母的话,明白那土炕、灶火、熏年糕的全部意义。它们不单抵御自然严寒,更是以最朴素坚韧的方式,对抗生命漫长无情的冬季。窑里珍藏的,是温暖、是食物、是希望,更是一种活下去的沉静和耐心。
如今,我的冬天有充足的暖气,随时可买的各色甜点,可灵魂总在“大雪”时节感到无可名状的饥寒。我渴望的,是那方被柴火与体温煨透的土炕,能把我半生漂泊的风尘寒气熨帖成安然的温热;我寻觅的,是那块被时光与烟火耐心熏染的年糕,需要等待才能获得的厚实甘甜。
终于懂得,祖母摩挲炕席的手,摩挲的原是一整个被疼爱的、暖烘烘的童年。而我这半生的乡愁,便是从窑口逸出的、一缕再也抓不住的烟。
作者:李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