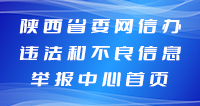“大雪”已至,雪还没有半丝音讯。
陕北的冬,一进大雪节气,便多了几分凛冽的笃定。天干冷着,像一块搁在窗台上许久的硬糖,糖霜早被北风刮得干干净净,只剩硌牙的干涩,在舌尖咂不出一点湿润的甜意。连空气都带着黄土高原特有的颗粒感,吸进肺里,凉得人胸腔发紧,却又干燥得掀不起一丝水汽,唯有鼻腔里总萦绕着淡淡的沙土气息,那是这片土地亘古不变的味道。
玻璃窗上蒙着一层模糊的白翳,不是雪,是夜的寒与昼的暖在玻璃上反复拉锯后凝成的细密水珠。呵一口热气,白雾在玻璃上漫开又迅速消散,指腹轻轻抹开一小片澄明,院前那棵瘦骨嶙峋的柳树便跌进眼里。它的枝丫光秃秃的,像陕北老汉青筋暴起的手,在灰扑扑的天幕下执拗地伸展着,静得有些哑然,连一声叹息似的摇曳都没有。树皮上还留着秋末的虫蛀痕迹和夏日暴雨冲刷的沟壑,此刻在干冷的风里,更显苍劲与孤寂,仿佛在默默细数着季节的更迭。
雪像一个吝啬的、犹疑的梦,只在节气单薄的纸页上,积了厚厚一层。记忆里,毛乌素沙地边缘的雪却不是这般。那时的雪是莽撞的、慷慨的,带着陕北人骨子里的豪爽与热烈,总在某个沉睡的夜晚,悄无声息地越过长城的烽火台,穿过榆林老城的街巷,将天地捂得严严实实。清早推开门,一股凛冽的寒气扑面而来,一片炫目的白便猛地扑上眼睑,凉沁沁的,带着新棉被似的蓬松香气,混着黄土的醇厚、沙柳的清冽,还有窑洞里飘出的糜子面香味。
屋檐下悬着晶莹剔透的冰凌,长短不一、粗细各异,在稀薄的阳光下闪着冷冽又纯净的光。小娃娃们呵着白气,在结了冰花的窗上画小鸭子,画歪歪扭扭的大树,画远处飘着炊烟的烟囱。
空气里嗅不到一丝雪的清冽,只有北风贴着榆林老城的城墙根,刮出“沙沙”的、干燥的絮语,像在反复擦拭一件蒙尘的旧瓷器。城墙砖缝里的枯草被风扯得簌簌作响,泥土板结着,露出粗粝的纹理,那是黄土高原独有的肌理,坚硬却又藏着生生不息的韧劲。路边的沙蒿、沙棘末梢焦黄卷曲,风一过,便发出极轻微的、近似断裂的脆响。远处的毛乌素沙地在灰蒙蒙的天色下,显出一片沉寂的黄,那些近年来栽种的樟子松、杨树,虽然依旧挺立,却也少了几分生机,叶片上蒙着一层尘土。于是便有些惘然,像守着一封约定了日期的信,期盼一场大雪——雪是来年庄稼的墒情,是牲畜过冬的棉被,是孩子们冬日里最盛大的玩具,更是黄土高原休养生息的契机。万物都在等,等一场酣畅的覆盖,等一次柔软的相拥,等雪将这片厚重的黄土地温柔地裹进银白的襁褓。
这等待,让人无端地生出一种秩序错位的焦虑。古人的二十四节气绝非简单的时令标注,而是一套集天文、气象、物候、农事于一体的精密算法与行动指南,是深植于东方智慧的生态农业操作系统。在漫长的农耕时代,这节气更是被陕北老百姓奉为圭臬。它不是文人雅士吟花弄月的诗意消遣,而是黄土坡上春种秋收的生活法典,是窑洞里柴米油盐的日常节律。
祖辈们按着节气春耕夏耘、秋收冬藏。大雪时节便该囤好过冬的口粮,将窑洞烧得暖暖和和,给牛羊备好干草,一家人围坐在炕头,捻毛线、缝棉袄,听老人讲那些关于长城、关于毛乌素、关于节气的古老故事。那时的节气,是刻在骨子里的生活准则,是融入血脉的生存智慧,指引着陕北人在这片贫瘠却厚重的土地上一代代繁衍生息。
花知时而开,人顺势而立,与天地唱和,与万物相谐——节气中所体现出来的“天地人”合一的共生之观,是华夏子孙共有的文化传承,在陕北这片土地上,更显得尤为真切。静水流深,绵延至今。古人云“大雪,十一月节。大者,盛也。至此而雪盛矣。”“小雪封地,大雪封河。”此时的陕北,本该有千里冰封、万里雪飘的盛况,无定河的水面该结起厚厚的冰,长城内外一片银装素裹,连呼啸的北风都带着雪的清冽。至少,入眼处,皆是琼花碎玉、银装素裹。书上的墨字规整而笃定,我们便按着这祖传的节拍,预备着围炉,预备着煮一壶滚烫的枣茶,预备着将晒干的红枣、核桃摆上桌,预备着一段炉火燃烧人心暖的诗意时光。可天公却兀自沉默着,留我们在自己的预备里,显得有些过于殷勤,又有些无措。
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里说得倒宽容:“大雪而雪盛,盖以节气得名,非必是日大雪也。”原来,节气只是一个盛雪的“名”,一个为盛景预留的座位。雪来,是实至名归,是天地对人间期盼的温柔回应;雪不来,那名,便成了一个清空的、引人悬望的符号。我们执着于“实”的降临,却忘了“名”本身,也早已在千百次的吟唱与期盼中,有了自己的骨血与温度。这无雪的“大雪”,或许正是在教导我们,如何与一个“名”安然相处,如何在期盼与落空之间,寻得一份内心的平和。
这般想着,心里的那份空落,便渐渐被另一种东西填满了。不是雪,是一种更为沉静的、关于秩序与自由的体悟。天地的秩序,原就比人间的历书更为宏大,也更为机变。它不承诺必然的雪,只承诺必然的循环,与循环中偶然的、惊心动魄的美——春天的桃花会开,夏天的蝉鸣会起,秋天的霜叶会红,冬天的风雪也终会如约而至,只是或早或晚,或浓或淡。无雪,也是一种“应候”。它让我们看见干燥的泥土下潜藏的生机,听见清晰的枯枝折断声里蕴含的力量,感受一种毫无缓冲的、棱角分明的严冬的质地。这何尝不是一种感官的馈赠?
陕北的冬,本就该有这般分明的棱角。它不像南方的冬那般温润含蓄,而是带着黄土高原的坦荡与直接。冷,便是彻骨的冷。干,便是纯粹的干。每一寸土地都在直白地展现着自己的本真。这样的冬天,让人心生敬畏,也让人更能体会到炉火的温暖、热茶的醇香,体会到家人围坐的珍贵。
大雪节气的到来,不仅带来了宁静与祥和,更让人们心生归宁之感。归宁,是一种内心的平静与安宁,是奔波在外的人对家的渴望与向往。在陕北,大雪时节便是团圆的信号,无论走多远的人,都想着赶在大雪封路前回到家里,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面。大雪节气,是自然界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,它标志着冬天的深入与春天的临近,也提醒着我们要顺应季节的变化,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——减少外出,静养身心,积蓄能量,等待来年的春暖花开。
暮色将至,院子里,老枣树光秃秃的,枝丫上还留着夏天蝉蜕下的残壳,被风吹得轻轻摇晃,发出细微的声响。墙角的那丛沙棘,红果早已落尽,只剩下带刺的枝条在风中坚守。远处的榆林老城渐渐亮起了灯火,星星点点,在灰蒙蒙的天色下显得格外温暖。
那层期盼已久的银白,终究没有从云端筛落。但我仿佛已看见它了,它不在天上,而在无数像我一样的眺望里,在《诗经》“北风其凉,雨雪其雱”的吟诵间,在张岱湖心亭看雪时那“上下一白”的痴意中,更在每一个平凡的屋檐下,对一场洁白寂静的、温柔的期盼里。
雪未来,而“大雪”已至。它带着它所有“名”的分量,带着千年的文化底蕴,带着黄土高原的深情厚谊,沉甸甸地,落进了这个干燥的黄昏。我拉上窗帘,将一室灯火与无边的清寂,隔成两个世界。炉上的水壶开始幽幽地哼唱,水汽顺着壶嘴缓缓升腾,在玻璃上凝结成细密的水珠。那声音湿润、暖熨,仿佛提前融化了一场,只存在于名中的、浩大的雪。屋里的枣茶香渐渐弥漫开来,混着炉火的暖意,将整个寒冬都温柔地包裹其中。此刻,无雪又何妨?这节气里的期盼与体悟,这人间的烟火与温暖,早已胜过了漫天飞雪的盛景。
作者:韦慧娟